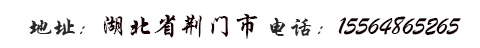晨读丨花逢盛世处处春浙江日报
| 曾经,养花有风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花,是奢侈的,与普通百姓无缘。那年月,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心思拈花惹草!整个村子没一个花坛,农家的屋角路边匍匐着的是“金瓜”“天萝”白扁豆,即便是唤做“花园里”的去处,也仅有塘边的几丛荆棘和野苎麻。倘偶有涉花者,即便养的是凤仙花之类最贱的草本,也会被旁人斥为不务正业。“十年”期间,养花更是高风险。记得当年村里有位姓卢的某大学助教,就因家门口有几丛祖上留下的夹竹桃,而被红卫兵戴上高帽批斗,据说其罪名是“游手好闲,生活腐化”。我家世袭与黄土打交道,养花本应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然,不知什么时候起,母亲从野外捡了一些“坟砖”“城墙砖”,叠在自家门口的天井旮旯里。一日,母亲用一个烂底的搪瓷脸盆种了一株叫“乐得跌”(像极了“接骨草”)的植物,竟成了破旧四合院最原始的花坛。这植株开小白花,叶子有股臭味,据说捣碎了可以治疗跌打损伤。就是这谈不上颜值的一盆药草儿,那时也是姓“资”的,说这是封建社会的“毒草”,是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者的玩意,不容分说被列为“四旧”给“破”了。后来,我母亲在这砖堆上架了块木板,改成了一个简陋的洗衣台。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实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生活逐渐得到改善,谈“花”色变的时代终结了,但经历过“百花劫”的人们大多心有余悸。一些胆儿大点的会在自家门口或天井里,用石块破砖圈点地盘,或拿出破瓦罐破脸盆什么的,种上几棵鸡冠花、菊花之类,但“犹抱琵琶半遮面”,总在空余的地方插种些葱蒜韭,或撒把菜籽,套种点小菜,以此掩饰花事。在乡村乃至县城的公共场所,那时仍看不见什么绿化带和花坛。记得只有在国庆、元旦这样的重大节日,有时南街老县府门口会用松柏枝和彩纸扎的花搭个彩楼,黉门广场会从远处拉来一些盆花,临时搞点花饰,节后便匆匆搬走。当时,“去黉门前去看花”是坊间最具诱惑的吆喝。真正意义上的养花,还是最近几年的事。在美丽县城和美丽乡村建设中,养花莳草成了百姓的家常事,各种各样的花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家。毫不夸张地说,当下城区各家各户的庭院简直都是小花园。我家才两间房子,院子虽不大,可也种着银桂、南天竹、牡丹、海棠、茶梅、胧月、半枝莲等廿多种花木,一年四季花香鸟语,蜂闹蝶舞。社区里一些庭院稍阔绰的还建有假山、鱼池,更是赏心悦目。同村的古稀老人傅绍平,嫌院子小,就用箍砧板的铁圈和废旧钢筋,建起了“立体花架”,向空中要花位,让庭院的盆景“站”了起来。昔日的穷乡僻壤,如今也处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不信?那就到南市街道走走——有山皆画图。大田头村的后山,月塘村的石金山,大潮村的纱帽头,南溪村的干山等,琪花瑶草与松杉柴荆融为一体,将一座座“癞头山”嬗变成花团锦簇的人间乐园。无水不文章。梨坑村的将军塘,岸上弱柳扶风,水中睡莲绽放。雅门村的门口塘,四围花木扶疏,青石雕塑屹立于水中央,巉岏的“悬崖”上盆花与碧水相映成趣。花墩塘村的花墩塘,水中3棵“千年紫薇”青春焕发,夏秋时节繁花似锦,动人心旌……上朱村的梅溪红叶石楠、樱花、月季与水中数以千计的锦鲤、石斑争奇斗艳。紫溪村的紫溪坑,一溪拖蓝,溪岸的数百棵桂花,夹杂着白玉兰,每至中秋,馨香氤氲,沁人心脾。凡村内有水塘和小溪的地方,多为景色迷人的风水宝地。绿杨芳草长亭路。这村村寨寨的通衢阡陌,无不花枝招展,简直就是一个个不断延伸的花园。廿里牌至后赵的千米“桂花路”,石盆村的步行“玫瑰路”,岘峰村的“百花路”,梨坑村的“杏花路”……正是这纵横交错的“花带”,编织起“三乡”大地的“美丽共同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花花草草的命运承载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岁月的沧桑。草绿是因春雨洒,花红全凭东风舞,只有新时代,才能催开万紫千红,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nzhiliana.com/bzlyl/14844.html
- 上一篇文章: 有了半边莲,敢于同蛇眠,5种对付蛇伤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