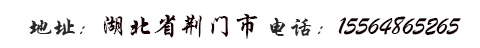李松山以放羊为生的ldquo牧羊诗人
|
北京那个白癜风医院比较好 https://m-mip.39.net/nk/mipso_4707905.html 李松山,年生,河南舞钢市李楼村人,放羊为生。二级肢残,小学四年级都没上完,这位今年39岁农民的诗作,被《诗刊》用11个页码重磅推出,一举登上诗人心中的“圣殿”。他的事迹曾因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广为人知。近来,又成为《诗刊》社第36届青春诗会的15位青年诗人之一。 我把羊群赶上岗坡我把羊群赶上冈坡,阳光在麦苗上驱赶露珠。我用不标准的口号,教它们分辨杂草和庄稼,像你在黑板上写下的善良与丑陋,从这一点上我们达成共识。下雨了,你说玻璃是倒挂的溪流,诗歌是玻璃本身。你擦拭着玻璃上的尘埃,而我正把羊群和夕阳赶下山坡。比喻让文字和麦子站在一起大多数时间我会邀请麦子走进文字在季节里我必须弯下腰用镰刀。像诗人码起一行行行走的文字一部分村庄是我的我也是村庄的一部分村口的麦田是我的我也是麦田的一部分这时候,如果有雪刚好落在我的遐思里我也将是雪的一部分倔强岗坡上的油菜花每一阵风来的时候,它们会抖几下这让我想起,简.爱中的简妮特以及她反抗,因为翻书而被皮带抽打的章节这一切像极了这些花朵预言时间在湖的平面上狂奔桨声划开日子最柔软的部分一只水鸟的预言被流逝的河床分解它立与冥想之上抖落青涩的记忆母亲她躬着身子将切好的土豆块埋进土里。种瓜得瓜,种豆不一定得豆。我的两个姐姐已出嫁,弟弟在杭州他们像土豆一样开出小花土地的忠诚,是值得信赖的。她笃信我有一天会成为丈夫,父亲说这话时,她的眼中,闪现一抹蔚蓝。高速的上空云朵飘忽,一个跳跃,从河滩跃过村庄在村后高速的上空,生出许多马驹。我瘸脚爬上岗坡,这歧义的生活。总有一些零星的雨,以露珠的形式和我接近。雨在小酒馆,我们谈论着词的多义和圆润性。像你诗中耀眼的句子雨珠伸出玻璃的舌头这时,窗外突然下起了雨:“噼里啪啦”,它也在复述这个荒谬的世界?沉默是无效的。雨在云的声带里奔突像你走进真实的自己,在笔端修复名词间的隐疾。畅想曲炭火已熄灭。月光在窗棂上勾勒出旁白。铅笔在酣睡,记忆里残留的雪,和几粒闪耀的星辰在稿纸折叠的皱褶里,无法邮寄。瓦房里深居的人,他推开门,露珠驮着阳光,在晃动的枝条间奔跑。自画像可以叫他山羊,也可以叫他胡子。在尚店镇李楼村他走路的样子和说话时紧绷的表情,常会引来一阵哄笑如果您向他谈论诗歌,他黝黑的脸上会掠过一丝紧张,他会把您迎向冈坡,羊群是 的动词;它们会跑进一本手抄的诗集里。说到风,他的虚无主义;会掀翻你的帽子,揪紧你的头发。你可以站着。或者和他一起坐在大青石上,而他正入神地望着山峦;像坐在海边的聂鲁达,望着心仪的姑娘。满月刚到河滩它就卧下了,胸脯和鼻孔像一个拉风箱。对于外界的事物,它有三分欣喜,二分的好奇,和五分的抵触。比如它会轻嗅野薄荷和半枝莲,露珠在草尖颤悠悠地晃。比如草丛突飞的野鸡,会让它惊慌,世界总是充满好奇和未知。像光芒中的艾薇,父亲眼中的一丝爱怜。注:艾薇,扬尼斯里索斯的女儿灰鸽子鸽群扇动翅膀上的的晴空它们绕过低矮的房舍,草屋上的瓦松与斜阳对视。那楼洞里仿佛有好多好多的鸽子。多少年过去了那栋老式建筑和鸽群早已不知去向,村庄正被城市袭来的钢结构越箍越紧。有人从郑州回来,说见到过它们一排溜站在高压线上,目光呆滞。也有人说,在南方见过,食客们打着饱嗝,一抹嘴。谈着股市和女人。其他当他写到自己的时候,突然停顿他竟无法描述一个真实的我。那么多词语敲窗而入,偏瘦。颠足。鼻毛伸到外边。像甬道里的打探者。暴雨过后,一棵构树苗,在微风里打着趔趄满是泥巴的枝条上,挂着几滴闪烁的水珠。蓝尾雀他在手机里读扎加耶夫斯基。沿着河滩向东,鞋底摩擦沙子的声音,和叶子簌簌落地的声音,仿佛来自某首诗的某段对话在辽阔的沉静中,形成一个横切面。再往前就是竹园地界:他停下脚步,两种声音仍在持续,几只蓝尾雀从低矮的草丛,飞向杨树林,杨树叶摆动枝蔓……重量我将带有花纹的石头,放进帆布包,放在两本书之间,石头和文字激起波澜;失重的叶子,落在湖面上;一只腐烂的麻雀,轻渺得让同伴忘记死亡。而当我把书放回书架;文字的风暴平息了,黑色的天平上,排列着纽扣的星星。灯台架一行数人,拾级而上。在半山腰,我瞥见从崖壁冒出一两束淡淡的白,它执拗地摇曳,在暗绿的阴影里随山的波度弯曲。飞瀑和石头,用清凉的土语交流。从凿石取火到LED只是落差明媚的一瞬。时间能杀死一切?哒哒的蹄声,踏碎多少尘埃?此刻我们在灯台架;在山巅的玻璃栈道上,如蜉蝣。在浩瀚的蔚蓝里。在李楼从北山到李楼,三站地的路程。长。不过一首诗的距离。我不止一次的给你提及李楼――越来越窄的村落,和越来越宽的荒芜。我们坐在村外的树林里。两打啤酒没喝完你就醉了,我惊奇地发现:两粒尘埃正从半空落下来,在杨树林;在生活的暗影里。在灵珑山他在石碣上讲述着:一抹绿茵从言辞的深岩中抽出嫩芽。他继续描述;历史在他的喉结稍作停顿,仿佛灵珑山的清泉,咕噜噜,冒着泡儿。我们在其间穿行,像鱼儿在绿色的波纹里拍照。留影,他们继续向山顶攀越。我则在几株茶树旁,停下来。呆如栅栏,波涛抚慰着它。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它会跟随羊群离开熟悉的河滩,到远一点的山岗。荆棘,蕨类,和针松让它感到新奇。它从岩石上跳到因断裂斜挂地面的松枝上而生活从来不缺少魔幻的戏剧性,刺猬团成刺球来抵御保护自己。水漂子的染色体会让它误以为那是一椴树枝。它卧在布满青苔的岩石上当然了它不懂苔花更不懂袁枚。它向下俯视,松涛的波澜,世界的白若隐若现。雨后空气潮湿,我站在院子里。鸟鸣声从周遭的树冠里落下来,如同树叶发出的叫声。我鼓起喇叭,朝它们喊了一声,声音仿佛来自某一棵树,某一片叶子。而滞留在紫薇枝头的雨珠,像静默的闪电,瞬间消失。中年凌晨两点,我从梦中醒来。却很难再回到梦中。墙壁惨白的光――深邃的玄学宇宙。此刻我卡在书架和床之间,听到蓓蕾挣脱襁褓像雪花挣脱云朵的庇护,并成为时间的污点证人。集市集市的路五里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硌脚,把往事硌的生疼花花绿绿的鞋子花花绿绿裤子花花绿绿的人群卖菜的大胡子把喉咙贴近喇叭那时,集市的路很窄从饭店挤出来的肉香味儿泼半条街那时,房子很低云朵很低人与人之间心贴的很近午后我在檐下喝茶,看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此刻,他望着远处,凝固的海,和流动的岛屿……一只麻雀在枯枝上鸣叫了一小会儿,它飞起来,像一个借喻,闪耀在我即将读到的诗节里闲下来的日子一桌人在搓麻将,一桌人在斗地主,一群来回走动的围观者。阳光落在坠落的叶片上,风抚摸着矮墙,低语。这是他们闲下来的日子,他们的麦子在各自的麦田里自顾自地生长,长势如何那是麦子的事情。小卖部后面的大桐树上,两只喜鹊在巢里不啼叫,不飞翔,它们闲下来的时候,和树冠融为一体。李松山3岁那年,连续高烧不退,患了脑膜炎,当时村里交通不便,只能在村医处弄点儿药。 ,病没能治好,落下了后遗症:口齿不清,走路趔趄,手指或强直如笔,或弯曲如钩。因为家穷,再加上三个学生,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看着松山这样儿,为了能让姐弟完成学业,四年级下半学期,9岁的李松山被父母接回了家。身体瘦弱又有残疾的他也不能分担太多的农活,便接过父母递过来的鞭子,赶着山羊走向了山根子下的荒冈……从此,辍学,放羊、喝酒、打牌、睡觉,成了李松山日常的生活状态。年夏天,弟弟李松林考上了高中,松山放羊回到家,看到父母的期盼,姐姐、弟弟的喜悦,高兴之余,突然产生了要为弟弟做点什么的想法。可作为残疾人的他又能干什么?冥思苦想后,他用自己再也合不拢的右手拉起弟弟的手说:“弟呀,哥——不能给你做——什么,从今天起哥也——要学习,给你做——榜样。”彼时,李松山15岁,已辍学6年,以前学的字,都忘得差不多了。“松山最令人佩服的是他的坚韧不拔。”舞钢市诗社成员东伦是李松山诗歌道路的引路人之一,对李松山了解颇深。为了能识字,李松山想到了别人完全想不到的办法——看电视字幕。电视上的同期声说一句,李松山盯着字幕看一行,把电视机当成带文字的听读机,一个字一个字,硬生生地记下来。电视节目不能回放,有时为了几个字,李松山都要等上好久的重播,或者其他频道的转播。过了大概十年,李松山买了手机,学过拼音的他如虎添翼,在电视上看到的字,记下读音,用手机打出来对比学习,再写到练字本上记忆;喜欢看诗、读诗的他,还存了多本中外诗集,整日沉浸在诗歌的海洋之中……这一过程,李松山坚持了整整21年。年8月,李松山尝试着写的几首小诗被李楼村塔后组的一位村民读到,巧的是这名村民与当时的舞钢市文联主席有旧,在他的牵线搭桥下,李松山的诗 次迈出了家门。结交诗友,李松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山羊胡子。从此,李松山再也不是那个放羊之外喝酒、打牌、睡觉浑浑噩噩的青年。他的生活状态常是这样的:蓝天下,羊在吃草,他躺在草地上,脑海里“生长”出一句句诗。有了“事业”的李松山,残疾、贫穷还有别人的嘲笑都不放在心上,心态平和,整日倘佯在诗的海洋中。脑海中不停跳跃着诗之精灵,一首诗不停地生长,成熟就是一瞬间的事儿。经常是酝酿几天,哪天早晨,大脑无比清晰,一首诗便完整呈现。“我只把它记下来就好,我只是语言的奴隶,从来不干涉它自由成长。”李松山诗的世界如此简单。一旦诗作成型,李松山就用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nzhiliana.com/bzljg/9017.html
- 上一篇文章: 番茄随笔I五月的鱼鳞滩
- 下一篇文章: 治疗肝癌,常用中医偏方秘方大全上